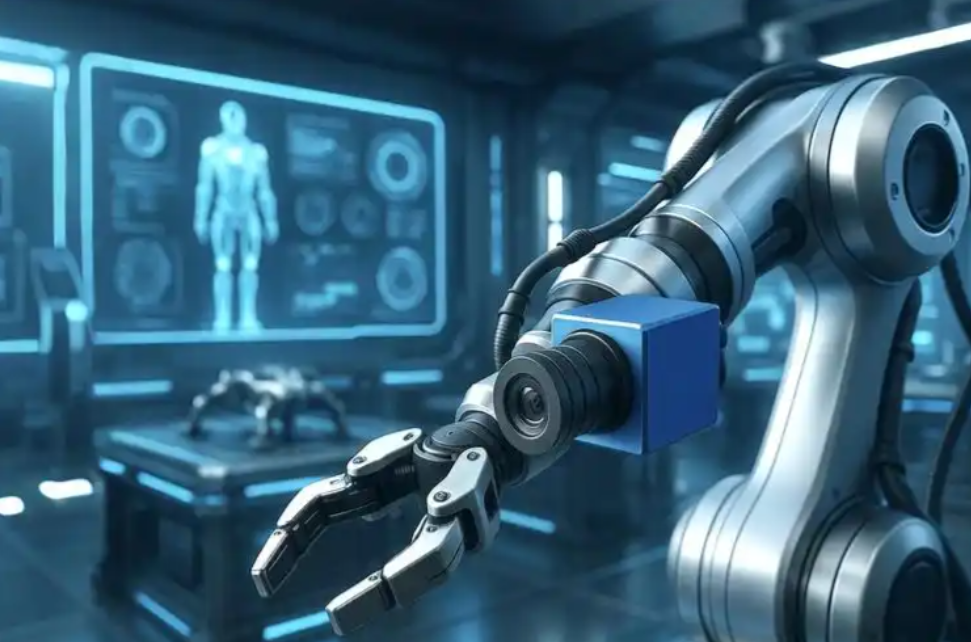“6年3倍DPI,基金不做二期了”
最后投资圈流行一句话叫:年后再说。这句话是投资圈拒绝项目最体面的托辞。年关将至,很多人一总结发现浑浑噩噩:募资募不到钱,投资投不出去,反投前置,管理费后置;宾馆变成全季,星巴克保不住金星,财务更新了全新的报销流程,同事们互相建议最好别出差。投资的职业弧光,此时暗淡无光。
“年后再说”也有理论依据。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列斐伏尔在其著作《日常生活批判》一书中指出,工作、家庭和私人生活、闲暇活动,三要素组成了人们的“日常生活”,并强调,“生活需要表达,而这些表达往往集中在一些特殊时刻,这些时刻就是节日。”
用来“表达”的节日,扮演着“放大生活瞬间”的角色。列斐伏尔认为,节日能让人在紧张的日常事务之外得到适当的舒缓和休憩,帮助人们表达自我、释放内心。
理论归理论,金融时间线,可从来不用自然年断代。更何况,金融从业者坐一起,不聊工作,聊什么?大家都是见过物质美好的人,都是有追求冲动的人,话赶话,绕着工作外围说半天,没词了,只能扯回来。
“我们不做投资了!“B君特别平静地说。
那你不做投资,做啥?还在一线苟着的Y君问道。
最近在做风水和面相。说什么会做投资,会看项目,都是命也都是运。个人能力也有一点吧,不多。
怎么的?你们的基金业绩一般啊?
Y君有一段做LP的经历,也做过募资。大体上,对于两方视角都有所了解,一般基金运营不下去,多数是业绩不好,或者募不到钱。原因可以理解,GP在一期基金,角色没有从做项目的投资人转换到基金运营者。
B君喝了一口茶,工作没了,在高贵调性一点儿没丢,这茶叶必须得是凤凰单枞,肉桂香。茶盏搁下,继续唠嗑。
业绩不算差吧?B君撇了Y君一眼。
那是多少呢?Y君穷追不舍。
六年的基金2-3倍,Dpi还行吧。
很好了啊,还要什么自行车呢?
在Y君的记忆里,关于GP的考核,可以按照2018年断代。2018年以前,GP募资,都会给LP看IRR——理想情况下,LP能拿到多少钱。
然而LP逐渐发现,在真实操作中,基金运营的每一环都会有费用产生,到退出的时候,扣除税费以及carry,LP拿到手的钱跟当时计算的数据有很大出入。且IRR在计算中,时间是要素。时间越短,IRR越高,更直白地讲,IRR是一道理想主义计算题,理想都在纸上,富贵也在纸上。
2018年后,LP要DPI,主打简单粗暴,不留操作空间。Y君当LP那几年,正赶上这场苦涩的转折,访谈了大量运营7-8年的基金,在那些有头有脸的名字后面,高情商地写着,“不到1”。
那为什么不做了?Y君好奇地问。
LP指手画脚,降低了我们的回报。
LP一般不太管啊?钱给了,后面就是一些日常沟通了。
Y君忍不住回忆起这些年写在尽调报告里的那些基金名称,一轮游的不是少数。但是,原因要么是投得不好,要么分配不均——嫌弃LP多嘴,这倒是第一次听说。
再加上LP是封闭的圈子,过去来自社会财富金字塔尖那1%,现在是身兼重任的产业资本和政府引导的资金,标签描述得再模糊,也很容易被识别、然后对号入座——这钱是要还是不要了?
我们小基金,LP少,LP在有IC的投票权。后面闹到基金牌照都不要了,反正一期做完,就不做了。
现在LP都成存量市场了,是不是应该忍忍?
这碗饭不好吃。B君深呼吸,好像有很多要说,但最后还是一阵长叹:前几年还舒服点,这几年关系太难处了。
多大的分歧,才会导致一个业绩碾压80%同行的优质GP,放弃跟LP合作,甚至放弃了第二期基金?茶馆面基结束,Y君当晚就失了眠,盘算起很多问题。比如GP怎么看待“专业性受到挑战”?放弃合作的过程有没有反复博弈?当初怎么就轻而易举地给了IC投票权,现在又觉得不妥?当初跪了,如今为何不继续跪下去?
有些问题好理解。比如LP的投票权,当LP在基金里占了较大额度——例如40%以上——出于对自有资金的保护,约定好要了一票投票权。
有些事情很难理解。比如LP真的使用投票权,假设游戏规则是,必须全员通过才可以投资,那么LP实在是太容易和GP产生分歧了,因为实际运营中,LP做不到深入产业,也没有人手去研究、学习——LP购买的是“理财项目”,GP玩的是“胜率游戏”,两者的终点,天然不重合。
投资圈在上一个周期有强烈的FOMO心态,也令LP和GP形成“对抗”的伏笔:一旦投资人发现错过的项目带来了巨大回报,“对抗”就会显化。甚至,带来对抗的常态化,即只要你提出的,我就反对。自然有可能合作不下去。
Y君翻来覆去睡不着,想起了去年8月在成都参加的一场投中闭门会,主题是《国资到底应该做LP还是GP》。这场闭门在公众号上推送的时候,被编辑们加了一个子标题叫,“历史已经给过答案了”,灵感来自天府科创投总经理张璐。
张璐说,国资最早进入创业投资领域是做GP的,后来发现国资机制下很难做好,才演进到做LP,所以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,是否要把过去走过的路再走一遍?
聊到后面,他打开话匣子,给出了一条建议:国资不一定要琢磨怎么去做GP,而应该下功夫把GR的工作做好,梳理好政府对产业的诉求,当好“翻译官”,帮助GP更好的完成“既要又要还要”。
Y君觉得,张总的话还需要继续“翻译”:做LP和做GP需要的技能大为不同。GP侧重于对行业的研究和理解,LP更重要的是“识人”。当然,过往的市场总会认为,“识人”是找到能投出好项目的人,后来发现,这就跟“好学生”不一定能带好团队一样,规模越大,可能基金越差。投出好项目,不等于能运营好基金,项目是业务,运营是管理。
说白了,表面上是“把自己的钱交给别人管”的不信任,骨子里还是对专业的不尊重。
中国私募股权的编年史从1985年成立的中国创业投资公司,到1993年熊晓鸽创办的IDG,再到2005年红杉中国成立,又到2015年的泥沙俱下、一涌而上,算起来40年的时间里,只容得下GP们在不断地责问中跌跌撞撞,来不及LP拥有“自我修养”,成为一套循证的体系方法论。
Y君不仅一次地听到过同行抱怨,LP直白地说我投你,是为了教学费,以后自己做GP,我给钱了,你得给我开放学习名额——就像找抖音大V教你如何一个月涨粉100万。
Y君也经常听到LP把投资比喻成选择题,认为选项是既定的,自己只要给出选项就能博出概率。
Y君希望求证这个观点,一激灵从被窝里坐了起来,点开了八卦群跟大家分享了B君的选择。同事们觉得这个观点稍微有点怪,因为循环是必然的,推动这些转变的因素有些是主动的,有些是环境加持。一位前同事说,他甚至觉得“LP”不仅方法论做不到一脉相承,就连“LP画像”都做不到一脉相承。
如果一定要断代“LP”的发展史,姑且可以概括为:
-懵懂时代。最早选GP相对简单,考察合伙人背景,做过的明星项目,多少项目上市了。至于赛道,就是撒芝麻,先进制造、消费、大健康什么都配一点。
-加码时代。双创时代带来了足够的基本盘,也带来了资本市场更完整的烦恼,于是GP筛选越来越严苛。再加上很多LP因为各种情况default,上市退出难度加大,S份额各方面也压榨的很厉害,投基金的时候也越来越谨慎,门槛越来越高。老GP的基金复投要比新GP要容易些,新GP尤其是第一支主基金的GP在选择时就很小心,但老GP的cross fund、DPI、退出等都又有不同的要求;原来国资要求作为最后一个出资LP,GP也有很多自主决定的权利。
-内卷/内耗时代。现在市场化的LP也和国资LP一样,互相担心default的情况,要求作为民营LP最后一个出资或者大家同步出资,如果有违约LP也会要求有赔偿条款,很多事情GP也不能自主决定,需要咨委会、顾委会或者合伙人会议;
再比如关键人士以前只锁投资期,现在需要覆盖到除延长期外的整个存续期;如果人工比较充裕,还会关注创始人的风格、团队、内部磨合,想法一致性,有没有背对背等等,也越来越看重基金的投后(对LP和对项目的)等等。
“一言以蔽之”。前同事在手机上敲了很久,对话框上反复出现对方输入找那个,“对于GP的挑选,就希望是在风口上站着的那一批,又希望是跑的快的那一批,但又不希望跑的太快。”
这是暴论。
过了半晌,有人在决定在群里小心求证:很想采访一下完整的经历过基金周期的人,对于现在的情况怎么看?
很快群里有一位仁兄回复说:02级的打个卡,没见过这么破烂不堪的。
仁兄喃喃道:
大家都是资本市场的NPC。成为LP是一种选择,是一种处境,它就像人类前行试错的火种,需要梦想和信念。LP可以成为大师,但没必要。GP不一定要成为大师,但没选择。
Y君想到了“给岁月以文明,而不是给文明以岁月”这句话,延续的商业文明似乎理应伴随着一次又一次的“LP学费”,不断地积累,以告知后人。
Y君决定小酌一杯,再给曾经的自己倒上一杯,杯子碰到一起,都是梦碎的声音。



 猎云网
猎云网
 投中网
投中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