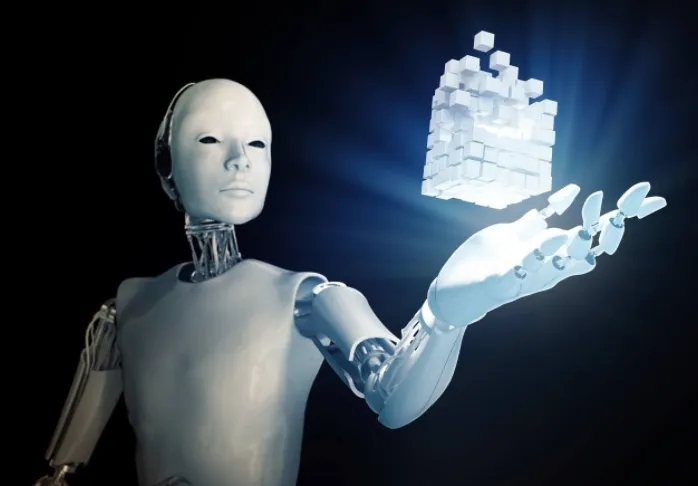马斯克:想打你脑壳的主意,但他放了鸽子,招募7位科学家只剩两位
令人失望的马斯克发布会
美国时间8月29日,埃隆·马斯克站在一台酷似苹果产品的神经“缝纫机”旁,显得有些紧张。2020年的Neuralink发布会开始了。
这台手术机器人能将宽度4μm-6μm的柔软电极丝编制在脑神经内。这些电极如此微小,宽度仅相当于人头发丝的1/10,还如此柔软,以至于能随着果冻般的大脑摆动,而不至于损伤神经。每分钟,会有6股电极丝(每股32根电极)织入脑内,一个电极阵列则包含96股丝(3072根电极),将人们能植入脑的电极提高了一个数量级。
这些电极末端,连接着Neuralink发布的LINK 0.9芯片。相比去年,这次芯片不再需要外挂在耳后,而是微缩成一个23mm*8mm的小圆盘,植入在颅骨内,对3072根电极传来的信号数字化。植入物可续航24小时,并且能无线充电。
在秀完这些以后,被植入柔性电极的真正主角——三只小猪出场了。当小猪用鼻子嗅东西,植入的Neuralink就能读取与鼻子上神经有关的信号,展示出一个脑电波高峰。而另一只猪运动时,屏幕上能显示运动的信号,甚至预测其关节的活动。
马斯克在去年7月说过,希望这项技术能在2020年底植入到人类患者身上。这次他则透露,Neuralink已经获得FDA(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)的突破性设备认证,“希望它能恢复残疾者的行动能力,解决老年痴呆症、中风等其他疾病。”
但彭博社指出,FDA希望不易移除的医疗设备至少能在人体中使用10年,目前这些柔性材料还做不到。此外FDA的其他许可仍未就绪,因此真正投入医疗仍未可期。
Neuralink能治疗什么?按马斯克今年的陆续放料,癫痫病、帕金森病、强迫症、成瘾、抑郁症、自闭症、肌萎缩侧索硬化病,以及其他形式的脑损伤都在可能之列。
今年7月,甚至有Twitter用户问马斯克,能否用Neuralink直接在大脑中播放音乐,马斯克回答“可以”。当用户问能否用Neuralink远程召唤特斯拉,马斯克回答“当然,当然”。但当被问道“Neuralink能为烹饪艺术做什么?”马斯克终于没能接下去。
尽管前景无限美好,自发布之日起已经不断有专家指出:Neuralink的工作仅在采集神经信号上,在信息解码方面并无突破。本来,脑机接口大体可分为四个步骤:信号采集、信号解码、再编码、反馈给大脑。
根据媒体报道,清华医学院教授洪波指出,Neuralink在神经信号解码方面没有任何进步,只简单演示了小猪四肢运动和脑内神经放电的关系。从马斯克的演讲可以感受到,他对神经编码原理不是很关注,对其难度的认识不够。妞诺科技CEO戴珅懿则表示,“马斯克的方法仍在传统技术范畴,能降低现有技术的成本,但离‘治疗’还存在相当长的距离。”
根据《WaitButWhy》此前一篇深度调查,科学界的普遍评价是:“在攀登脑机接口这座大山的征程中,Neuralink是一支装备精良的登山队,并非坐上了直升机。”
一个佐证是,Neuralink在2017年就曾与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进行猴子研究,但至今仍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猴子成功操控了计算机。2019年7月,Neuralink在预印本论文网站bioRxiv上发表了一篇论文,作者为“Elon Musk, Neuralink”,但对大鼠实验的实际效果讲述得十分模糊。而与此同时,已经有其他研究者成功用人机接口技术控制计算机光标,输入信息甚至点一杯咖啡了。
为什么创办Neuralink?
尽管业界对于这样的发布感到失望,但也有人为马斯克辩护,一个理由是Neuralink本就不是为治疗创办的。它是为了在大脑和机器之间打开一条“高带宽”传输通路,加快人类与AI的结合。因此相比信号解析,大规模采集信号才是关键。“好数据总是好过好模型”,如果数据足够多,机器学习也许能完成解析工作。
Neuralink采用的柔性电极网概念被称为“神经蕾丝”,来源于苏格兰科幻小说家伊恩·班克斯的《迎风舵轮》,指的是在大脑植入一张筒状的网,让神经元在网中生长,从而实现人工电极和神经元的共生。
2016年,马斯克创办了Neuralink,面试了超过1000人,最终招募了7位顶尖科学家。他们是:
Paul Merolla,IBM的SyNAPSE计划首席芯片设计师,擅长根据大脑结构设计晶体管电路;
Vanessa Tolosa,生物相容性材料专家,擅长根据集成电路设计生物相容性材料;
Max Hodak,BMI(脑机接口)专家,创立有生命科学机器人云实验室;
DJ Seo,在加州伯克利大学发明了神经尘埃-小超声波传感器,即用超声波捕获神经信号;
Tim Hanson,“地球上最好的全栈工程师之一”,擅长材料科学和微细加工方法;
Flip Sabes,擅长皮层生理学的BMI专家;
Tim Gardner,曾在鸟类脑中植入BMI,并通晓神经元活动模式。
但据医学新闻网《Statnews》披露,算上马斯克,如今上述科学家也只剩下3位了。其中1位还表示“马斯克的技术更适合基础研究,推动人类使用为时过早”。马斯克则称对方没有成功留在公司。相比医疗公司,Neuralink的工作节奏“快得像高压锅”。
为什么创立Neuralink?这与马斯克的AI焦虑相关。他创立了Open AI非营利组织,以监控AI的发展速度,预防人工智能的灾难性影响。但这远远不够,因为监管是缓慢而线性的,AI却是指数进步。如果不能有效遏制AI的负面影响,不如在AI超越人类前与它融为一体。
在Neuralink团队不久前的一次采访中,马斯克解释了这种逻辑:人类的思考非常迅速,但交流信息却十分缓慢。“这就像用一根针头喝一杯奶昔。”通过图片,我们可以看到,计算机彼此之间交流的速度远胜过人类。即使人类自己的思考,速度也超过说话、手写和打字一个数量级。
人与计算机的交流速度对比
相较于思考过程,人的表达速度十分缓慢
“如果带宽太低,那么你与AI的集成将非常薄弱,AI只能自己走了,因为它对你说话太慢了......AI不是‘其他’,而是你,类似于大脑皮质与边缘系统的关系......沟通速度越快,你将融入越多;沟通越慢,则越少。”
因此,高带宽就是AI与人类之间系着的绳子。如果这根绳子足够粗,人类就能充分绑定AI的能力,而不是被它抛弃。在与Neuralink的对话中,“带宽”一词出现了42次。
Neuralink还关系到人类的AI平权。马斯克将AI视为“终极力量”,它会导致一部分人比另一部分人更强大,而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让AI融入每一个人。如果无法避免人们制造“魔棒”,那就只能创建一个开放、协作、透明的魔棒实验室,将魔棒的技术分享给所有人,而非少数人秘而不宣的武器。
对此,马斯克提出一个口号:“By the people,for the people,of the people”。这是AI时代的“民有、民治、民享”。
Neuralink的愿景实现路线图
当然,对这样虚无缥缈的理论,从不缺乏质疑。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学名誉教授Noel Sharkey称,AI只是一种工具,没有证据表明它们会崛起并消灭人类。美国新南威尔士大学人工智能和数据教授Toby Walsh认为,人类总能以情商和社交能力、创造力和适应力胜过AI。Facebook人工智能部门负责人Jerome Pesenti认为,马斯克在批判AI方面不知所云,现阶段根本无法想象通用人工智能的存在。
脑机接口离人们还有多远
脑机接口的一个好处在于,它不像特斯拉或SpaceX触动了传统石油和工业巨头的利益,因此能相对自由的发展。1978年,William Dobelle博士成功地在一位后天失明的病人脑中植入电极,让他可以看见黑白色的低分辨率图像。在这位先驱后,脑机接口的实现从未停止。
1982年,Hugh Herr在一场滑雪灾难中失去了双腿。后来他成为MIT媒体实验室生物机电工程领域的负责人,开发出设备并重拾对攀岩的热爱。2014年巴西世界杯,最著名的脑机设备亮相:凭借美国杜克大学的设备,一位身穿机械战甲的截肢者成功在绿茵场上开球。
脑机接口的原理并不复杂。神经元活动时会吸入足够多的阳离子,引起细胞表面极化的改变,从而生成电位。电极则能捕捉这种电位,但捕捉的方式各异:有的在脑中直接插入电极(侵入式),有的隔着厚厚的各种皮层和头骨(非侵入式),还有的放弃大脑直接捕捉肌肉的电信号。
侵入式电极最显著的问题是要开颅。你很难大规模劝服健康人,因此它主要用于患者身上。Facebook创始人马克·扎克伯格就曾表示,“我们会有手接口和语音接口,甚至还有脑接口…但这不会以一种侵入式的方式进行。”如果要做侵入式,你肯定会上新闻——就像马斯克做的。
侵入式电极也无法对应足够多的神经元。人的大脑中有860亿个神经元,而类似半导体行业的“摩尔定律”,脑机接口也有一条“史蒂文森”定律:我们可以记录的神经元每过7.4年增加一倍。如果按照这个速度,直到2225年,人类才能记录大脑每个神经元。而即便能全部记录,大脑中也塞不下这么多电极。
另一个问题是,人们对大脑的活动原理知之甚少,无法将神经元活动对应到具体行为上。哈佛大学分子与细胞生物学系教授Jeff Lichtman有个比喻,如果关于大脑的知识是一英里,人类现在只走了三英寸。但机器学习的进步,使人们有可能不需要知道中间过程,只需根据大数据的统计,对应起输入和输出。
相比马斯克的激进方式,大部分其他公司比如Facebook都在研究非侵入式电极。它的好处在于适宜普及,且容易做实验。坏处在于对脑电信号的分辨率太低——就像隔着瓶子听蚊子叫。它本质上捕捉的是多个神经元同步放电的一种模式,能关注到高级认知层面对注意力对象的控制。
但问题在于,对于高级认知任务,注意力对象只能有一个。因此非侵入式脑机接口只能做到分时而非分频。相较健全人们的沟通方式,这种方式更加低效,显然不适合马斯克“灵体交流”的高带宽任务。
不同脑机接口的时间和空间分辨率
此外,侵入式和非侵入式脑机接口面临的共同问题是:人们对脑机接口的研究还局限于“脑-机”层面,对“机-脑”一无所知。简单来说,人们知道一只老鼠如果想喝水,就会有46个神经元兴奋,因此监测这46个神经元就能控制饮水机。但如何将外部机器的信号编码成神经元信号,反过来输入给大脑?对于大脑这本“词典”,人们只知道有文字,却一个字都还不认得。
因此无论Neuralink的发布是福音还是灾难,都距离人们尚远。新南威尔士大学人工智能和数据教授Toby Walsh认为,毕竟马斯克以不能按时实现承诺而闻名,针对健康人的神经联结或许要等到几十年以后了。
猜你喜欢
特斯拉人形机器人产量将大幅提升 我国现存机器人相关企业已超81万家
马斯克称AI影响巨大,预测人形机器人Optimus产量将大增,最终价格不到2万美元。我国现存81.1万余家机器人企业,广东、江苏、山东最多,超七成成立于5年内,0.8%企业涉司法案件。



 博望财经
博望财经
 东四十条资本
东四十条资本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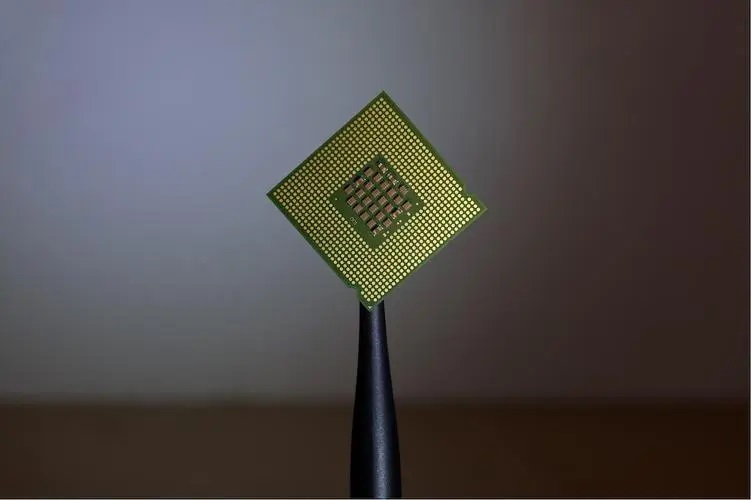
 猎云网
猎云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