博实乐退市:三年半私有化拉锯战落幕,小股东博弈失败
作为曾市值超百亿美元的中概股“明星”,博实乐的退市不仅是一家企业的转折点,也是中国民办教育资本化进程的一个缩影。
01
政策风暴与资本撤离:教育资本化模式的瓦解
博实乐的兴衰与政策演变密不可分。
从鼓励社会力量办学到严格限制资本介入,政策风向的转变直接决定了教育企业的资本命运。这一转变过程可分为三个关键阶段,每个阶段都对博实乐的经营战略和资本市场表现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第一阶段是政策红利期(2017-2020年)。2017年,《民办教育促进法》修订完成,明确实行非营利性和营利性分类管理,为教育企业资本化打开制度空间。同年9月实施的《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》进一步细化了扶持政策。博实乐正是在这一政策窗口期成功登陆纽交所,发行价10.5美元,市值一度飙升至近30亿美元。借助资本力量,博实乐开启快速扩张,2017-2019财年营收从13.28亿元增长至25.63亿元,学校网络迅速扩大。
第二阶段是政策收紧期(2021年)。随着《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》修订完成,明确规定“不得通过兼并收购、协议控制等方式控制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”,直接冲击了博实乐的商业模式核心。据《新学说》等多个渠道报道,博实乐被迫剥离旗下多家幼儿园和双语学校,这些业务在2021财年贡献了约60%的营收。政策冲击立竿见影,股价从2021年初开始一路下行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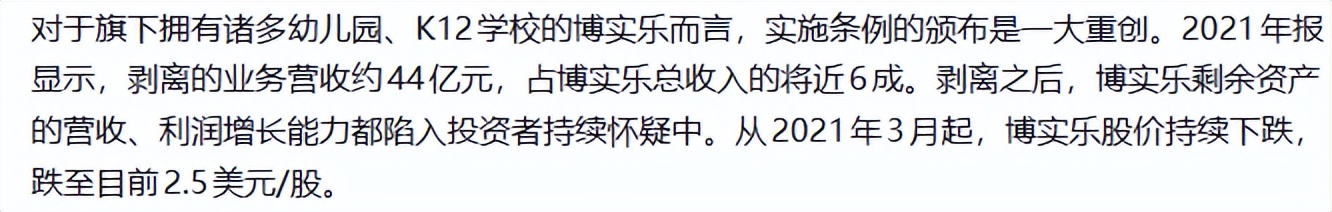
第三阶段是政策落地适应期(2022-2025年)。在政策明朗后,博实乐开始业务转型,重点发展海外学校业务和补充教育服务。然而,资本市场信心的恢复需要时间,股价长期低于1美元,最终在2022年3月收到纽交所退市警告。尽管基本面逐步改善,2021-2024财年毛利率有所提升,但政策不确定性已深刻改变了投资者的风险偏好。
02
私有化博弈:大股东与小股东的利益拉锯
博实乐的私有化过程是一场典型的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博弈,这场持续三年半的拉锯战不仅反映了公司治理结构的特殊性,也揭示了中概股在海外市场面临的估值困境。整个私有化过程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,每个阶段都体现了不同利益相关方的策略调整与博弈焦点。
私有化进程的第一阶段(2022年4月-2022年底)以“低价试探”为特征。由杨惠妍和杨美容组成的买方团提出每股0.83美元的收购价格,较当时股价溢价,但相比发行价10.5美元缩水92%。这一报价引发小股东强烈反对,认为“严重低估公司价值”。值得注意的是,杨氏家族当时持有博实乐78.06%股份和92.52%的投票权,这种股权结构使得小股东在传统投票机制中处于绝对劣势。在巨大争议下,买方团最终撤回了私有化提案。
第二阶段(2023年-2025年5月)是“策略调整期”。随着博实乐业务转型初见成效,海外学校业务收入在明显增长,公司价值支撑有所增强。但股价仍长期低迷。这一阶段,买方团调整了策略,将报价降至每股0.50美元,但同时引入了更具争议的法律工具——开曼群岛公司法下的“短式合并”条款。这一法律安排允许持股超过90%的大股东在满足特定条件时,无需少数股东批准即可强制收购剩余股份,极大降低了交易完成的不确定性。
第三阶段(2025年5月-10月)是“交易收官期”。在最终协议中,收购对价提高至每ADS2.30美元(约合每股0.575美元),相对公告前收盘价溢价近五成。据《公司研究室》报道,有部分小股东认为,博实乐因“双减”政策影响,股价长期低迷。即便加上一定的溢价,仍未完全反映公司的长期内在价值,特别是其正在增长的海外学校业务的真实价值。

然而,在“短式合并”机制下,小股东的议价能力被大幅削弱,最终只能接受交易安排。
总结
博实乐的退市标志着中国教育行业资本化浪潮的退去,预示着教育去资本化时代的正式来临。这一结局不仅是一家企业的个体命运转折,更是整个行业发展的缩影。
从行业发展趋势看,教育去资本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。2021年以来的政策调整根本性地改变了民办教育的资本生态。博实乐被迫剥离义务教育阶段业务后,虽然加速向海外学校和补充教育服务转型,但其商业模式已发生本质变化。这种转型虽然带来业务结构的优化,但也意味着公司从原来的“地产+教育”模式转变为纯粹的教育服务提供商,失去了原有的协同效应和规模优势。
博实乐的退市是教育行业资本化实验阶段结束的标志性事件。它展示了在政策主导的行业环境中,资本与教育结合的局限性,也为其他教育企业的资本路径选择提供了重要参考。
未来,教育企业的发展将更加注重政策合规性和社会效益,而非单纯的资本回报,这或许是退市事件带给行业的最大启示。
猜你喜欢
博实乐退市:三年半私有化拉锯战落幕,小股东博弈失败
作为曾市值超百亿美元的中概股“明星”,博实乐的退市不仅是一家企业的转折点,也是中国民办教育资本化进程的一个缩影。



 博望财经
博望财经



